韩啸:雅士的刀与血
来源:《风度》

脱衣,剃发,洗濯。
划线,抹药,麻醉。
亲手做完这一切,韩啸穿上洁净的黑衣,俯躺在手术台上。
麻醉药效很快起来。在他的示意下,手术正式开始。头发被一根接一根地拔出来。每拔一根,就有一滴血从头皮里冒出。血珠,黄豆般大的血珠。剃过后的头发只有两厘米长短,拔出后被放置在托盘里,交由一旁显微镜边的助手进行分离清洁。头发不断被拔出,血不断冒出,纱布不断擦拭又很快被血浸透,再换一块继续。这一切都通过现场的摄像机投影到大屏幕上,每一根头发被拔出的情景都清晰可见。
压抑,紧张,围得密实的观众,开始有人不堪忍受血肉模糊的拔发现场而离开。包括那些在他做准备工作的时候,咔嚓咔嚓拍照的好奇观者。
但一切有条不紊。大约半小时后,他坐起身来,开始进行手术的下一阶段——植发。
植发本是正常的整形美容手术。但今天这一场手术的“不正常”之处,在于发生地点,以及人:地点是798里赫赫有名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;主人公是韩啸。他是手术者,亦是被手术者。所以,这不仅仅是一场手术。这是一场表演,一场精心准备的行为艺术。
再次打了麻药后,他上半身倚靠在手术椅上。麻利地接过助手递过来的小针管,在镜子帮助下,一次又一次地插入头部,轻轻一压压,头发进入头皮。一旁的助手再用镊子拔出少许,恰如新生毛发长成。就这样,韩啸自己把200余根毛发逐步植入前额,发际线,发髻角。
韩啸让自己成为了被观看的中心。这是他的主场,他的艺术表达。
尽管,对于这样的手术是否属于艺术创作曾经有过不少争议,且争议仍持续着。
尽管韩啸自己说,是否是艺术,或怎样去定义都是无所谓的。但他的创作并未有过停歇。此前,他已经先后举办了《手术:韩啸行为艺术展》、《整形:韩啸行为艺术展》、《今日不做整形—韩啸艺术展》等展览,获得了关注与成功。他踏入了一个新的圈子。

尽管北京的当代艺术已经很发达,但韩啸的行为艺术还是显得先锋前卫了一些。由医生而成的艺术家不多,一般多寄情于传统的书法或是山水画,像韩啸这样半路杀出来,还走当代艺术范儿的,也算是屈指可数。也因此,阻力不可避免。毕竟,他不是科班出身,更像是一个外来的搅局者。他倒是淡看了争议和批评,或者说,这正是他想要的。在他的观念里,艺术在当代语境里就是要介入社会,对社会发生作用。这种基于身体的行为艺术,若是能够引起大家对整形和对身体哲学的思考,在他而言已经足够。至于是不是艺术,可以再探讨。
他甚至不喜欢贴“艺术家”这一枚标签。在一次对话里,他还喊出了:“你才是艺术家,你们全家都是艺术家”。虽然颇有些标题党,倒也可窥见其态度。他说,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做好玩儿的事情。
mu:你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是什么?
韩啸:我是希望通过努力掌握更多自由。自由,就是适应世界的能力。当然,只要去做就会是不自由的。所以一个人很难脱掉最终的既定的命运。但我想要的还是自由。吊诡的是,当我不需要得到的时候,才会容易拥有。一旦放弃的时候,才会真的得到。所以我试图通过多元,一种兴趣的多样性来获得更大的自由。
mu:财富、名气、健康、相貌,你每一样都具备了。那你有没有比较遗憾的事情?
韩啸:如果我小时候就接触了法语、德语等多门语言,我三十岁的时候可以周游列国,很好地去享受一切。但出身于草根阶层的人,很难有这种适应社会的能力。所以富家子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,也许不是更多的机会,而是待人接物,把握机会,适应社会的能力。修改自己童年既定命运,这个过程太痛苦了。
mu:近期的计划?
韩啸:接下来会在欧洲有几个展览,分别是在捷克的国家美术馆的行为艺术展,芬兰的行为艺术展,卢森堡和西班牙两个画廊的作品展,然后是佛罗伦萨双年展。之后就直接飞往美国,参加迈阿密的巴塞尔博览会。
mu:作品的方向呢?还是以行为为主么?
韩啸:我现在的作品大多和身体相关,以行为为主。但之后我希望我的作品更多和生活相关。茶、酒、精致的生活,把这些元素纳入到艺术创作中来。你看,就算是斗蟋蟀这样的行为,也需要比较精致的器具,这也是一门艺术。我想探讨的是,艺术可以不是生活,生活可以不是艺术。或者说,我的生活高于艺术。
风流自赏,只容花鸟趋陪;真率谁知?合受烟霞供养。
谈传统文化里的美学,清人涨潮的《幽梦影》应该在必读书清单中。“风流自赏,只容花鸟趋陪;真率谁知?合受烟霞供养。”这句话出自《幽梦影》,也是韩啸比较属意的自我勾勒。这也不是一句空谈。在培养自己成为雅士的路上,韩啸走得认真。凡是雅的事情,他都要一试。他迫不及待地往前走,仿佛是要摆脱身后破落低矮的茅屋,快步奔向一栋金碧辉煌华丽无比的雕花大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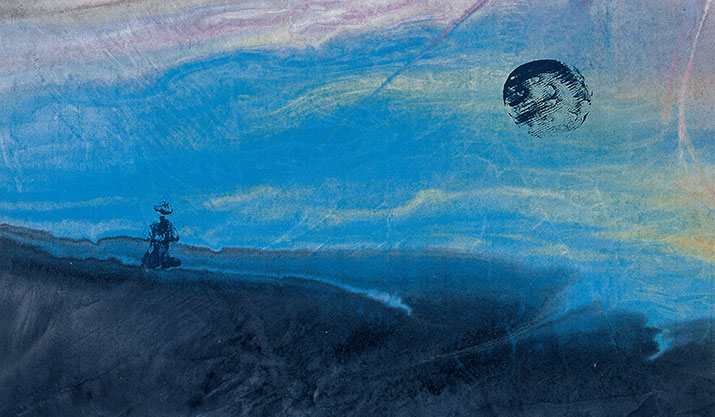
除张潮的《幽梦影》之外,韩啸屡次提及的还有两个人,两本书。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。袁枚的《随园食谱》。文震亨是明朝大书画家文徽明的曾孙,家学深厚。一本《长物志》实际上是一本艺术博物志,分为了室庐、花木、水石、禽鱼、书画、几榻、器具、衣饰等十二类,文字简洁而娓娓道来,自是名士风雅。
袁枚的《随园食谱》是中国古代的厨界经典,其中列为十四单,开篇讲作料之选,“善烹调者,酱用优酱,先尝甘否;油用香油,须审生熟;酒用酒酿,应去糟粕;醋用米醋,须求清冽。且酱有清浓之分,油有荤素之别,酒有酸甜之异,醋有陈新之殊,不可丝毫错误”。饮食之趣也正蕴藏在这挑剔的精致之中。
学问之道,先知而后行,饮食亦然。袁枚如是说,韩啸如是行。他怀着巨大的热情研读食谱,又高薪聘得一位大厨,每日里与厨师探讨这厨灶之事,乐此不疲,还在微博里“表白”对这位大厨的爱意。吃喝玩乐,没几个人不爱。一般人也就简称自己是一枚吃货,听闻哪里有好吃馆子就涌去饕餮一番。韩啸却是以问道的精神来吃饭,“嗜美食”又“近庖厨”,“欲享乐必躬亲”,研究做菜也拿出动手术的气势来,还上升到了哲学层面。不独是美食,美酒,美服,美器,美人,但凡常人所知的美的事物,他是通通都不错过。他喜欢穷其究竟,还喜欢躬身实践。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居住之所,环铁艺术区的一个Loft,主色调为白色,大厅的水泥地上是水墨山水画,这也是他亲手以墨涂之。
传统意义上,四十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,“四十而不惑”。韩啸也自拟了篇《四十自述》,文言风格,且颇为自得。他以谪仙自居,写自己“嗜鲜衣美食良器靓婢健仆”,“爱洁、香草、居山林”。看书写字,吟诗作画之余,或把酒言欢,或周游列国,或斗斗蟋蟀,十足的传统文人作派。这谪仙的生活自然普通人也是难以企及。
mu:有人说你是“温柔的法西斯”?
韩啸:这个说法是多么的悖论啊。其实也有些形象,可供想象的空间很大。外表是温柔的,其实比较狠。医生都比较狠。我说的狠,是指在我的领域里,我必须要说了算。当别人上了我的床,就是进了我的地盘,我得做主。这里面可能也隐含了狂热、权威、征服的意味吧。当然,我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。

韩啸:俗话说的烂桃花嘛。经常有男性在微博里私信我,有点尴尬。这算是一种公开回应吧。我没有不尊重这个群体,但也请不要老骚扰我。
持刀造美的医者
医者韩啸,科班出身。如今衣香鬓影,谈笑自若的他,却并非家世甚好的富家子弟。
韩啸本科毕业到某三甲医院工作,期间去山东医大修读硕士,并承包科室创业。一个小小科室到如今一万余平米的一座整形医院,中间的艰辛有多少?他极少提及。当初不得已辞职的无奈,街头发传单的艰辛,这种创业血泪史已只会偶尔出现在朋友间零碎的闲谈中。从烧伤专科到整形美容,这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切换。其中的商机当然是肥美的诱惑。当然,对美的追求,也可算是一个积极优雅的理由。
十年间,他做了逾万例的手术,“无一例的医疗事故”。
现在回想起来,他说那是疯狂的岁月。一个人做三个人的活儿,什么都要极致的好。这种完美主义倾向的生活代价巨大。一天10台手术,尽管助手们做好了术前各种准备,很多时候他“只需要过去咔嚓一刀”,时间仍然排满。颈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,以致于手术中头不能自由转动,需要护士帮忙扶着他的头,轻轻替他转。
白天挤满了手术,夜晚则焦虑思考不能入眠。这个每天给人动手术的医生,终于把自己折腾到了病床上。先按照颈椎病治疗,伽马波照射,他一夜醒来300多次,不见效。又换了种方法,取出了鼻下的某个组织,还是不见效。两个手术后,他戴上了呼吸机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,晚上睡觉呼吸暂停时常发生,状态危险。
有朋友提出建议,他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,与医学完全无关的。按照一种医学说法,只有让大脑的另外一部分兴奋起来,过分兴奋的一部分才会得到压制。什么是与医学不同的事情?艺术。用艺术来治疗疾病,倒把他引向了一条向阳的幸福大道。生活轨迹从此改变。

财富在累积。心态也在变化。他说自己终于可以选择做手术的对象了,不入他眼的人,他可以拒绝。他又时常调侃,“没有20万,不要想上我的床”,大笑。
他还批判整形圈不太关注人性,只是把人当作物件。手术的评断标准就只是直观效果,而不是为受术者整体形象塑造的价值。他说整形就是韩国比中国好,为什么?他觉得核心是对人性的尊重,中国的整形圈“需要人性的重新回归”。技术并不是最大的问题。于是,他极力鼓动身边的同仁也去修读美学课程,也去学习艺术,希望能够把艺术的内涵融入到整形美容手术中。穷则独善其身。他坦言,以自己的性格和能力,在当下的中国环境里,恐怕难以推动什么大的变化。但他又特意区分了脑力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差异,并以萨特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来阐释自己。他对于时事侃侃而谈,还把“厌专制,抗暴政,宣普世,远功名”写入自己的小传。为浊富而不为清贫;以忧生不若以乐死。他要的却是,站着把钱挣了,还要忧生乐死两不耽误。
mu:你曾经说过,“整容是神的手段,是造物,是道路,是真理。”能谈一谈这句话么?
韩啸:这话耶稣说的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,我就是真理。可怕就是在这。尼采说,“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,这就是我与你的不同”。整形是包括设计的,对肉身的设计和改造。医生用手术刀去改变别人的身体,这里面有一种很具体的神圣感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,我觉得合格的整形师太少了。我觉得该有一点宗教性,也就是虔诚性,要持有超凡脱俗的敬畏之心。
mu:你一直都很痛苦地看待自己的职业?
韩啸:你只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,就很痛苦。幸福来源于要求不高。我现在正在学习如何粗糙一些。有的时候,也许也不是粗糙,而是简单。可能不痛苦吗?我觉得可能。安迪沃霍尔说,人最快乐的时候,就是把生活中填满了全神贯注的性。吃饭的时候只想吃饭的事情,看书的时候只是看书,那样我们的生活就可以不用这么嘈杂。

